《聖母峰之死》作者眼中的臺灣隊爬得慢、技巧差,隊友遇難時不立即下山處理這點也招致批評。單看這本書,會認為高銘和這種行為於情於道義上有點糟糕,但讀完高寫的《一座山的勇氣》,又會感覺當時不下山,是很正常的情緒反應。
臺灣隊不同於霍爾及費雪帶的商業隊伍,是雜牌軍,八百萬元經費也是花兩、三年以上奔走籌措才湊齊,資源非常少,還臨時被通知聖母峰路線再次向大眾開放,路線費用激增40%左右。出國前,兩個隊友突然對高銘和說他們晚點去,從加德滿都往基地營途中,不時有兩光隊員走錯路,很晚才到目的地,感覺很鬆散(這跟高的管理方式有關吧。據他自己描述旅途各個情節,可推知他不是很高壓的隊長,隊員愛幹嘛就幹嘛)。到達基地營後,還有人因練習攀爬時覺得很累,成天跟他吵著要下山,他也讓對方下山了。不久後該名隊員又出現在基地營,高也只是說一句:「喔,回來啦。」跟霍爾嚴實保護客戶的作法天壤之別。
高的書後三分之一主要在講山難跟他治療過程。整本書讓人覺得高是個散漫但是個性很有趣樂觀的傢伙(看Youtube紀錄片,也有外國觀眾留言說高銘和很有趣,可見應該不是我眼光怪異吧)。
《聖母峰之死》

我正在穿靴子準備上到四號營,台北來的三十六歲鐵工廠工人陳玉男爬出帳篷上大號,但只穿著登山靴的平底內襯,這是嚴重的誤判。
他蹲下時在冰上失足跌倒,一路滾下洛子山壁…。他雖然受到擦撞,嚴重驚嚇,但似乎沒受重傷。在當時,霍爾隊的人(包括我在內)甚至都不知道有這起不幸。
之後不久,高銘和和與臺灣隊的其他成員將陳玉男留在帳棚內養傷,讓兩個雪巴陪他,然後出發前往南坳。儘管霍爾和費雪以為高銘和不會在五月十日攻頂,但這位臺灣隊隊長顯然改變了主意,打算跟我們同一天出發。
那天下午,有個拖運物資到南坳的雪巴人江布在折回二號營途中特意停在三號營,他查看了陳玉男的狀況後,發現他的病情已經惡化到認不清方向,且痛苦不堪。江布斷定他必須下撤,就找了另外兩個雪巴人一起護送他。他們沿著洛子山壁,到了離冰坡底部九十公尺的地方,陳玉男突然側身倒下,失去了知覺。過了一會兒,布里薛斯的無線電在下方的二號營響起,江布以驚慌的口吻報告陳玉男已經斷氣。
布里薛斯和他的IMAX隊友韋斯特斯衝上山看能不能救活他。他們大約四十分鐘後抵達陳玉男身邊,發現他已沒有生命跡象。那天傍晚,高銘和抵達南坳,布里薛斯用無線電呼叫他說:「馬卡魯,陳死了。」
高銘和答道,「好的,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布里薛斯大吃一驚,他氣沖沖地說:「我剛剛才替他闔上他朋友的眼睛。我剛剛才把陳的遺體拖下來。馬卡魯居然只說聲『好的』。我不懂,我猜這也許跟文化有關吧。也許他認為繼續攻頂才是緬懷陳的最好方法。」
《一座山的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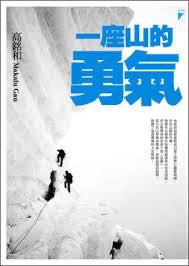
吃過飯,我和陳玉男又再躺下,打算等雪巴們把裝備收拾好便出發。
沒多久,陳玉男說他想上廁所,我告訴他不用走太遠,直接在帳篷旁邊解決就可以了,在這高山上,一切都是自自然然,不用不好意思。陳玉男說了聲「好」就出去了。大約過了十來分鐘,美國IMAX隊的一個雪巴章木在不遠處喊我的名字,問我們是不是有一位隊員不見了。我愣了一下,撩開帳篷,沒有看到陳玉男的蹤影。章木才對我說:「你們的隊員滑到下面去啦!」
我嚇了一跳,心裡很焦急,但因為腳上沒有穿鞋子和冰爪,也不敢一下子就衝到外面,只好儘量把身子往帳篷外深,想一探究竟,卻甚麼也看不到。我大聲喊我們的雪巴,卡米和巴山立刻從帳篷衝出來,當他們弄清楚是怎麼回事,馬上穿鞋子走過來。我趕快把身體轉回帳篷要穿鞋子,不料動作太急,摩托羅拉對講機天線卡到帳篷給折斷了。我趕緊把掛在脖子上的瑞士刀拿下來,想用它來換對講機的天線,哪知道拿下來的時候,掛著瑞士刀的繩子-那正是丹僧納旺活佛送給我的「參地」-竟在這刻斷了。我的腦海快速閃過一絲不祥的念頭,但這時沒有時間多想,立刻把斷掉的「參地」重新綁起……陳玉男的情況好像不太嚴重,只向下滑了一小段就停住了。
(中略)
我問他有沒有怎樣,他說還好,但有點累,想喝水,然後就自己到水喝。雪巴則幫他把冰爪脫下來,讓他好好躺下休息。
於是我們兩個又一塊躺在帳棚內。我再問他有沒有覺得哪裡不舒服,他說沒問題,但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好像右邊有點痛,於是我叫他趕快自我檢查一下。他自己東摸西摸後,還是說沒有甚麼問題。
(中略。到了上午八點)
…卡米來告訴我,準備動身要往第四營移動了,於是我告訴陳玉男:「雪巴要出發了,我們準備一下,衣服穿一穿就上去啦!」
哪知陳玉男突然說:「隊長,我看你先上去好啦,我想再休息一、兩個鐘頭後再上去。」
「怎麼了?有甚麼不對勁嗎?」我聽了馬上問他。
「我覺得有點累,想多休息一下。」陳玉男有氣無力地答著。
(中略。下午三點多,當時高銘和已抵達南坳)
就在我和旺久及隊員們用無線電相互通話之際,突然插進來IMAX隊長大衛的聲音,他告訴我:「馬卡魯,我是大衛,你的隊員陳玉男,大約一小時前就過世了… …」
聽了這個消息,我先是愣了一下,頭腦一時轉不過來,只急著向他說了:「謝謝,感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也沒時間、更不知道像大衛多說甚麼,只知道要旺久趕緊去查證陳玉男到底怎麼了,但過了許久一直沒有進一步的消息。這時,我只覺得這是個不正確的消息,帳篷外的風雪越來越大,我、明瑪和剛進來的丹增一起坐著壓住帳篷,真怕它會被風吹走。雪也越下越大,我們心裡都十分沉重。
大概是五點鐘左右,基地營的秀秀打無線電來,斷斷續續說了一句:「隊長,陳玉男已經走了……」然後是一陣哭泣聲。聽到「已經走了」四個字,我立刻呆若木雞,話也接不下去,愣愣地坐在帳篷中,整個腦袋思潮洶湧,但又好像變成一片空白。對講機一直在呼叫著,我也忘了要去回應,這時的心情亂到無法控制。
太突然了!再怎麼想也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中略)
帳篷外的風雪絲毫未見減弱,而我的心情也跟外面的風雪一樣紛亂。一個令人難以取捨的問題在我心底盤旋:要不要繼續攀登?陳玉男出事了,照理說我應該下去第二營處理善後事情;可是想到好不容易才來到八千公尺地第四營,如果明天照舊去登頂後再下去,只耽延一天,但能完成這一次遠征目標,對社會大眾較好交代。再說,陳玉男已經確定走了,晚一天下去處理也影響不大。如果現在就往回走,有點功虧一簣的感覺。
我也知道,以我們現在的情況,只要一下去,就沒有再往上爬的士氣和機會。… …
發表留言